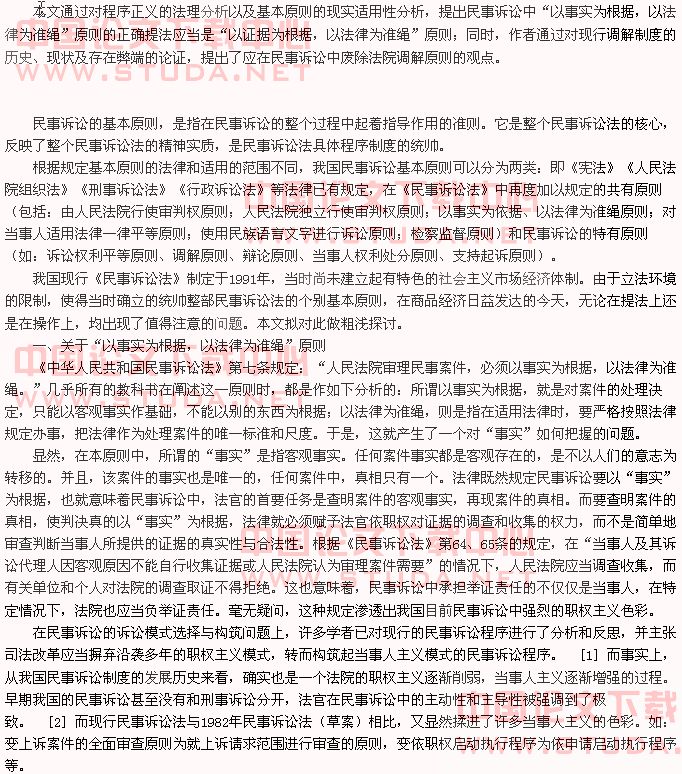
应选择何种诉讼模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对此也争论颇多,本文对此不多做讨论,但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指导下”,法官依职权所享有些调查取证权却值得质疑,它显然会带来很多很难克服的弊病,甚至影响到了程序的公正与正义。
(一)法官依职权取证,改变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力量对比,破坏了法官的中立性。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在诉讼中所享有些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也是平等的。产生争议的双方有责任对我们的倡导负举证责任,在没办法举证证明我们的倡导时,则将面临着举证不可以的不利后果。法官作为裁判者,则需要维持中立,并以一个居中者的身份对双方的证据进行审察和判断,而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所有这类,构成了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
而法官的介入,则显然破坏了这种力量的平衡。第一,在法律规定当事人平等举证责任的状况下,法官为查明事实真相,依职权主动取证,其结果势必是增强了一方当事人的证据证明力,而使他们当事人所举的证据相对弱化。于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平等便因法官的主动参与而遭破坏,其结果可能是:一方在没办法证明自己倡导的状况下,却因法官主动取证而免予承担举证不可以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另一方当事人在拥有优势证据的状况下,却因法官的主动取证而面临败诉的局面。这一来,“哪个倡导,哪个举证”的原则事实上已因法官的主动参与而可能流于形式。第二,法官主动取证破坏了一个裁判者应有些中立性。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案件的事实全部由法官查清的状况几乎没有,所以,无论法官所调取的证据对哪一方当事人有利,他在无形中都是已将自己置于他们当事人的对立面。所以,法官主动取证,事实上是在案件事实未查清之前,已经偏向了一方当事人,于是作为裁判者所应具备的中立地位便因此丧失。从程序上而言,中立是裁判公正的生命,当中立丧失时,其裁判的公正性是值得质疑的。
(二)法官依职权取证,使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就所获得的证据公平辩论的机会,使得法院成为民事争议的矛头指向。
因为法官处于一种裁判者的地位,所以,即便法官所获得的证据存在缺点,他们当事人也不可能就该证据是不是合法有效与法官进行公平的辩论。于是,这就产生如下情形:法官通过取证证明某事实的存在或没有,又通过裁判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事实上是集事实的证明者和裁判者于一身。自己裁判自己所获得的证据合法有效,这本身就已陷入一种逻辑的混乱。
从程序正义上讲,其他人不能充当自己与别人纠纷的法官。所以,正当的程序需要法官应当是中立的,与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无涉的。[3]而当法官充当了案件事实的证明者之后,其对其所证明的事实便有了法律上的责任,也就是说,法官的中立地位已经丧失,不再与案件无涉。于是,对案件事实的争议也不再是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当事人总是将争议的矛头指向作出裁判的法院。
(三)在“以事实为依据”引导下,法官的依职权主动取证权,将使当事人举证不可以的状况下,案件的裁判探寻不到一个公平的落脚点。
尽管国内民事诉讼法仍保留了非常强的职权主义色彩,但在“哪个倡导,哪个举证”的原则下,法官却对案件是不是依职权取证享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即:在当事人没办法举证的状况下,法官既能够主动取证,也可以不主动取证,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就完全系于法官觉得是不是“案件审理的需要”,在这个弹性的规范规范下,无论法官作出何种选择,均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于是,同一宗案子,也会由于法官是不是取证的不同选择而产生完全不同的两种的结果。
司法实践中,在当事人没办法举证或举证不足的状况下,法官主动取证的状况还是比较少的,一般的做法是由当事人承受举证不可以的法律后果。尽管这种做法符合民事诉讼的特征,也为各国民诉立法所采纳,但从其次来看,大家却不难发现,这种诉讼规则与“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由于,“当事人没办法证明的事实”并不等于不是事实。于是,当法院觉得当事人举证不足时,事实上已探寻不到一个公平的落脚点:因为法官未能不承认该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而只不过觉得证据不足,那样,对当事人的诉求不予支持无疑不是依据“事实”,当事人也完全有理由抱怨法官不可以使调查取证权而使事实未能查清,并将这种怠于行使职权(或说是渎职)的后果转嫁给当事人;而法官也可以觉得当事人未根据“哪个倡导,哪个举证”的原则举证而将责任推给当事人。
假如说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法官为查明事实而主动取证是一种势必的话,那样,“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产生的另一后果就是:它混淆了法律上的事实与客观事实有什么区别,混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证据使用规则有什么区别。
所谓法律上的事实,是指由各种证据所支持的,对案件的处置结果有影响的事实。这种事实的认定以证据的审察认定为基础。于是,这便又涉及到一个证据证明力与不同案件证据规则不一样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因为犯罪行为侵犯的已不止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侵有国家的法律秩序。因此,为证明犯罪,需要由强大的国家力量参与调查取证,证明犯罪行为的存在或没有。即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成谅解也不可以阻止国家机关对犯罪行为的追诉。在诉讼实力上,公诉人与被告人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方,故此,法律对刑事案件的证据需要已达到“排除所有可能性怀疑”的程度。[4]
而在传统的分类上,民法是私法,贯穿民法一直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也衍生了诉讼权利义务的平等与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当事人在自己民事权利遭到侵害而不可以使诉权时,法院并不主动干预;法律甚至允许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撤诉与和解。为维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这种平等,法律强调“哪个倡导,哪个举证”。同时,因为诉讼双方诉讼地位、实力的平等性,法律不可以对其中任一方的证明责任提出更高需要,所以,对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需要事实上是远远低于刑事诉讼,法律对民事证据的需要远没达到“排除所有可能性怀疑”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法官要“以事实为依据”显然不现实。由于,只须存在就算是万分之一的其他可能性,就不可以觉得现有些证据所支撑的事实是客观事实。
与刑事诉讼相比,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事实上是一种优势证据规则。比如:A向法院提供一份由B亲笔所写的借条,请求判决B偿还借款,而B则倡导该借条是在A采取胁迫手段的状况下所写,但却无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胁迫”。于是,作为本案唯一证据的借条,事实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胁迫所写,一是自愿所写。但依优势证据规则,在B没办法证明“胁迫”事实的状况下,法院只能觉得借款事实的存在。虽然这是以证据为基础,也符合民事诉讼的特征,但却显然与“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相违背。若将“以事实为依据”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则意味着民事诉讼中,在当事人没办法证明自己倡导时,法院不可以简单的“不予支持”,而是负有证明其倡导的事实存在或没有的义务。即:须排除合理性之怀疑。但这显然与民事诉讼的特征相冲突,如前所剖析,其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与诉讼的高本钱和低效率。而即使这样,用证据证明的事实仍没办法与客观事实完全等同,而只能最大限度的接近客观事实;有的事实甚至没办法用证据来证明,而只能靠法律的推定,如当事人的默示与民法上的过错推定等。
所以,所谓“以事实为依据”,其实是用证据来证明的所推出的“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更准确一点讲,“以事实为依据”其实是“以证据为依据”。
笔者觉得,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改为“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1、当一方当事人证据不足时,法官依现有些证据作出判决有法律上的依据;
2、强化当事人的证据意识。
在这种规定下,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将重视保留证据,而不是依靠于法官事后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取证;
3、淡化法官的职权主义,保证法官的中立地位,从而保证了程序的公正;
在该原则下,法官将只负责证据的审察判断,防止民事诉讼法官的主动干涉而致使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失衡;
4、不至于产生法律上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混淆。
2、关于法院调解原则
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就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或通过协商而达成共识。
法院调解规范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这一规范的形成有直接用途的是中国成立以前解放区的纷争的裁判方法,即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法”。“马锡五审判方法”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案件的裁判者在深入群众,调查采集证据、知道纷争形成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和教育,最后解决纠纷(也即调解与审判相结合)。马锡五审判方法是对国内传统的民间纠纷的解决方法的直接继承和发扬。[5]在这种审判方法的影响下,国内民诉立法历来重视调解,并将它提到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高度来加以规定,如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原则”与现行《民诉法》第9条规定的“法院调解原则”等。
尽管法院调解规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计划经济年代起过不可替代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在产品经济日益发达、法制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是应该继续将它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却值得质疑。
[1][2]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