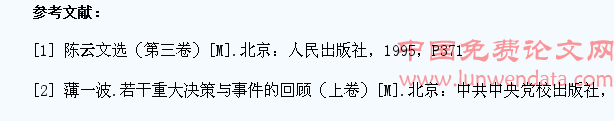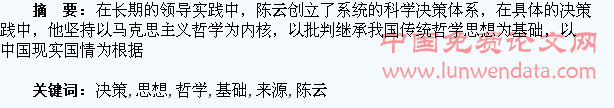
陈云作为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要紧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的很多重大决策,并且很多重大决策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陈云创立了系统的科学决策体系,并在具体的决策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点的陈云决策思想,为国内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实践典范。究其缘由,是由于他的决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的,是以批判继承国内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在中国现实国情上形成的。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陈云决策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来源
陈云同志擅长在实质工作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法、办法,因而看问题特别准,特别远。他通过总结、概括领导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极为深刻地讲解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第一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强调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觉得大家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打造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实践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重要的基本的看法,实事求是就是这种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概括。
陈云决策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这最鲜明地体目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字中。陈云说:“不唯上,并非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更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 就是只有从实质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置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1]陈云很看重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同决策联系在一块,他说:“大家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弄了解实质状况;求是,就是需要依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2]
最能体现陈云坚持唯物认识论的是他在决策中坚持“国力原则”。1957 年,陈云发表了《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觉得需要重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要维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平衡,从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来讲,要维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他觉得,按比率进步是最快的速度,有多大伙底就做多大的事,只有从国力出发和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才能提升社会主义经济进步的速度和效益。薄一波对当时的状况评价如下:“我觉得,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这类建议,是从实质出发,实事求是的,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办法指导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生动体现。”
(二)坚持认识运动过程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它把辩证法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坚持从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考察认识活动,它觉得大家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陈云决策思想不只体现了他坚持认识的唯物论,还体现了他一直坚持认识的辩证法。他把这种辩证的认识办法归结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交换,就是互相交换建议。……过去大家犯过不少错误,究其缘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质当成了全方位的实质。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常常同其他人交换建议,特别是多倾听反面建议,只有好处,没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假如没不认可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我们的建议愈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由于大家的认识,总是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对认识的辩证规律的精辟理解。
在决策中,陈云看重认识的两次飞跃及其往复无穷的过程。他觉得认识应该从对现实状况的深入调查开始,在获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剖析。“大家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状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依据对实质状况的科学剖析而来的。”[5]他十分看重将定量剖析与定性剖析相结合,处置经济问题时处处都用数据了解话,常以定量剖析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方法,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他指出,经济工作既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而对于那些实质状况比较复杂,通过定量、定性剖析预测仍难准确把握推行成效的重大决策,陈云强调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通过试验进行验证。他需要:“大家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非常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提出决策、检验、再决策、再检验的公式,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识规律在决策工作中的运用。他觉得,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方法,因而决策过程中需要做出个可供比较的策略,反复论证,择优使用。“从决策办法上说,他不只提出八种策略和办法,而且逐一剖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最后定出可行政策。从决策程序上说,他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慎之又慎。”
(三)坚持实践真理观。大家的认识过程是探求真理的过程。真理的内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检验真理的规范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因而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坚持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和进步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需要。陈云的决策思想坚持了实践真理观,坚持了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准则》的文章,其看法与陈云的思想不谋而合。对于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陈云给予了高度看重与支持,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准则”这个提法很赞赏,他三番五次地强调,毛泽东著作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陈云觉得,坚持真理需要不计个人得失,不可以搀杂个人好恶与私心。“假如所有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非常了解,不会讲真理,结果肯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只须有勇于拓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大家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2、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陈云决策思想的历史来源
陈云决策思想的形成除去拥有以上理论来源以外,还继承发扬了中国古时候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陈云历来看重哲学的学习,有学者从哲学性格、哲学观、哲学贡献三方面对陈云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讲解,觉得陈云的哲学性格可以概括为“实践性格”,表目前:从精神特质看,体现为应用哲学;从理论旨趣看,体现为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从思维模式看,体现为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从价值理想看,体现为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这类在陈云同志的一些著作和讲话中得到了非常不错的体现,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方位、比较、反复”,作为认识真理和解决问题的一个科学的思想办法和工作办法,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吸收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纵览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及其统一的传统。陈云在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加以批判继承,这主要表目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国内有“经世致用”出色传统,觉得学问需要有益于国事,强调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陈云在其领导决策中特别强调务实性。1939年12月,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陈云强调指出,学习理论必须要联系实质。老干部要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未来的工作。可见,陈云心目中的理论或哲学,决不是书斋中的学者出于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构筑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用途或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有用的理论。二是对中国古时候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中国传统“一分为二”的命题上,陈云的“用人的辩证法”做了非常不错的解释。他指出,要用全方位的看法看待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云觉得知道人的时候,不可以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目前,这都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办法,“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含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包括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进步,短处得到克服。总之,“天下没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缺点的,所以大家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三是对墨子、颜元、魏源等人关于认识源自“行”并强调“亲知”的唯物主义看法的继承。在这一点上,陈云的名言是“领导机关拟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已经足够。”状况明了是研究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首要条件和基础,而状况明了则是调查研究的直接结果。陈云常常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亲自体验,并反复实践。
3、中国现实国情是陈云决策思想的现实来源
所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贯穿陈云决策思想的基点。陈云之所以能在国内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缘由是他深谙国内国情。陈云决策的很多看法与倡导,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点在于从国内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剖析和判断状况,从而使拟定出来的政策具备要紧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一五”计划期间,陈云依据国内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基本状况,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等提出了系统的正确建议,粉碎“四人帮”将来,当中国人民刚刚迈开“四化”的节奏,个别领导人想靠引进搞“洋冒进”时,陈云又指出大家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需要改变生活。大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个现实的状况,是拟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实践已经证明,对客观存在的基本国情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把方针政策放在靠谱的基点上,从而卓有效果地领导经济建设。陈云觉得多年来,大家屡吃经济过热的苦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从实质存在的国情出发,单凭主观愿望,企图大干快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陈云倡导需要从国内现有些经济情况出发确定建设规模的大小。需要从国内的经济近况和过去的经验中研究国民经济的比率关系。早在五十年代,陈云就从经济工作必须要尊重国情的思想出发,针对已经出现过的“小冒”,高瞻远瞩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需要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大家如此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要紧。建规模超越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这一论断,意义极为深刻。他的这一倡导,不只指出了处置建设规模与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程度。而且提出了处置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与办法论,与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经济管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