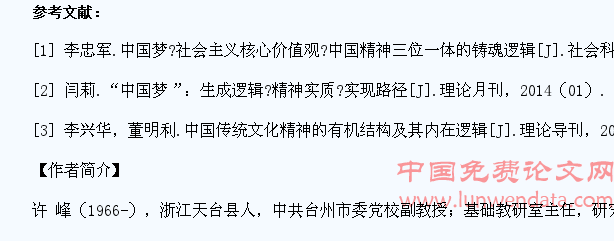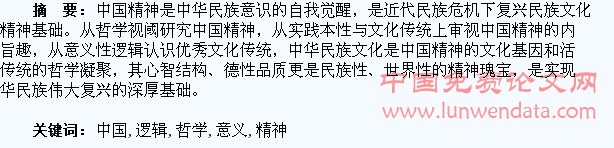
马克思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可见,作为民族文化信仰的要紧组成,中国精神所蕴涵的文化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所主张和追求的民族复兴实践,具备形而上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蕴涵多重意义的哲学性省思;同时,对于哲学省思,也非纯粹的出于哲学的偏好,而是基于哲学性的理解来重新审视中国精神的多义性和多重属性。当大家将中国精神作为哲学范畴定义来研究时,“中国精神”将是民族复兴实践性和年代性的具体体现,更是需要从其内涵性理解中来重新发现。
1、中国精神的内涵
近代以来,伴随东西文明的交互与冲突,对“中国精神”的自觉研究更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所激起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自省。以历史的见地来审视近代中国的进步,有识之士可以清醒的意识到,民族危机下的文化危机是激起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不竭源泉。悠久的历史文化,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全国过去和将来进行联结的时候,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精神,在面对现实性问题和将来理想的冲击中,又会经受抽象性的曲解考验。正如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危机的重创,研究并重新衡定中国精神的内涵及哲学本体,将成为目前中国常识界势必面对的最重要问题。辜鸿铭从中国人的精神入手,就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影响,再到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研究,统是“中国精神”哲学研究范式内容。马克思提出“人类一直只提源于己可以解决的任务,由于只须仔细考察就能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对于中国精神的内涵及挖掘,势必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基础,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自觉中来全方位把握中国精神的哲学本体和精神实质。
近代中国对“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印证了真的有价值的思想,总是是在异常沉静,甚至是忧患意识中获得,大家对中国精神的立场与认知,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世界性视线的现实期许,也只有在这种沉静且忧患的思想首要条件下,才可以客观而全方位的审读这一宏大的意识形式,维持真切的独特视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而达成中国梦,势必需要从中国精神的挖掘、弘扬和传承中来促进梦想成真。因此,研究中国精神,立足中国的特定国情,从“民族精神与年代精神”的内在统一上,借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当代中华民族具体实践,重新阐释和明确“中国精神”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在《习近平关于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达成中国梦需要弘扬中国精神”,而对于“中国精神”的理论研究及进步导向,将成为目前学术界集中探讨和挖掘、收拾的核心问题。综观中国精神的研究实践,主要呈现三种研究路向:一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明确“中国精神”;二是结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进步实践来深化和阐释“中国精神”;三是借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从文化自觉上来践行现实进步与文化精神的统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就“中国精神”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学者围绕中国精神的形成基础展开探讨,也有学者将中国精神的构成要点进行挖掘,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价值取向、建构模式上来进行梳理,还有学者从中国精神的科学进步与全方位弘扬上展开实践。无论是当下还是将来,对中国精神的深入研究为大家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认知和学术资源,但总体来看,更多的学者将视角投放在常识性和形成性范围内,对于中国精神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中,怎么样发展多样化价值追求,以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来重塑民族精神,怎么样从追求革新、超越自己进步中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精神信仰融入到达成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中。这类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中国精神民族性、文化性、价值性、信仰性的多重多义的整理。中华民族在达成民族复兴夙愿实践中,归根结底是在实践中来改变自我、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从实践意义上来强调中国精神的文化性与实践性属性的统一,更需要从出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精神具体实践进行融合。
2、中国精神的构成及活的传统
1、中国精神的文化构成
梁漱溟先生在探讨文化的意义时提出“样法”定义,对于哪种文化传统,从而决定了哪种生活方法及实践道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出色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儿”,也是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中国精神来源于对中华民族出色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是统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性、现实性、真实性的重点。中国精神正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股劲儿”,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华夏儿女一同的“根儿”。因此,认可并弘扬中华出色传统民族文化,就是承载中华民族“样法”的具体体现,是构成中国精神的要紧内容。从中国精神的内涵体系来看,怎么样挖掘和梳理中华出色传统文化,怎么样从“精神基因”上来挖掘“活的传统”?对于基因,生物学上是构成生命的基础单位,而对于“精神基因”,中国精神同样需要“精神基因”来维持文化的活力。中华民族在精神传统中的基础、最基本的精神基因又是什么?翻看中华的文明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道德境界中的“止于至善”、政治伦理中的“治国塑身平天下”、与天命精神中的“各正性命”等思想,都是中国精神的最棒的精神基因。从这个意义来看,对于当下中国,从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构成上来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性,更需要从强调“精神基因”中来适合的提炼“活的传统”。 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需要从文化省思中来洞见文化精神,从“精神基因”的探析中来总结“活的传统”,特别是从体现中国精神的出色文化中,以自觉的心理来理解和审视中国精神,及其出色的、深刻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是由历史和精神传统构成的,不同年代下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一同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本体和特质。在理解中华出色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时,怎么样从历史的、现实的文化价值尺度来客观、正确的评价、传承出色传统文化精神,势必需要从民族文化自觉上,从经验文化上升到道德文化,达成从“神道”到“人道”的转型。如殷周时期的“神、道”文化,先秦时期的“德、礼”文化、汉唐时期的“和、合”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心”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要紧组成,在文化生成、传承和革新实践中,怎么样从民族文化的自我审视中,超越文化冲突,将文化传统与对文化的更新、坚守作为达成文化内在连续性的引线,从文化的更迭、交融、借鉴、革故鼎新中来开启“救亡图存”的文化追求,进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达成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新洗礼和转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对古圣先贤的智慧的感性直觉,也是传统文化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直接反映。面对中国精神的博大文化,想要真切的体味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上,更看上去极为困难。如一个“道”字,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志于道”则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和探讨的核心难点。王阳明在探讨天地自然本然的玄奥时,提出“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对于“道”,并不是是大家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也非是确定性的结果;对于文化思想的认知,与其说是形上之“道”,莫若说是悟觉形上之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来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概括是极为困难的,而要真实而具体的表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从文化意向性思维和文化省思中来澄清定义,同样是复杂的。古时候思想家将“道”统之为宗,正所谓“道可道,很道,名可名,很名”,对于思维的表述与思想内容的彰显,需要从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空间中来高度浓缩,以穿透性的理解力来领悟和考虑中国精髓的特点、性情结构和思维特征,势必需要从文化自觉中来细数中华文化脉络中的“文化基因”。
道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落脚点和归宿,如天道宇宙论、生活道德修养论、社会道义实践论等,无不围绕“道”来展开,体现民族文化心理的进步方向。西方人在乎识形态范畴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作为西方哲学基础,而性情论、境界论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用理性来认知和理解世界,成为西方人的习惯性传统,如“理性世界观”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现,也是打造在西方社会“常见秩序”的契约基础。与此相反,对于中国人,在审视世界的时候,总是用德性的精神,以“天理”来支撑“良心”,通过道德实践来达成“和而不同”的伦理社会,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德性宇宙观”、“悟道思维”成为天人合一精神的主旨。一个人的民族文化观念与整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同样在心智结构上具备相似性。如“塑身、云筑网、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思想,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合适的,并成为生活修养实践的思想导向。具体而言,以“道”为核心的精神体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德性教化与人的性情修为作为心智结构的具体化特质。如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成为六种天性的缩影。其中《诗》代表情志、《书》代表政治、《礼》代表社会,《乐》代表艺术,《易》代表辩证,《春秋》代表历史。进一步来讲,六经不只悟觉人,更要紧的是对人的教化。《礼记?经解》中“其为人也,温顺敦厚,《诗》教也;疏公告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e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样来看,对于德性精神及中华民族的心智结构,六经的主旨与内容正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范例,也是构成中国精神的出色的文化基因。
2、中国精神的“活的传统”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人格、伦理、情感、实践、精神等各方面都为大家重新梳理文化逻辑创造了条件。较之于东方文化,西方人性论是打造在假设基础上,并从文化“自由”中来体现历史逻辑;中国的人性论是打造在“大同”精神基础上,两者在对人类内在本性的理解上都是打造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如中国古时候将“大同”理想凝聚为世代相传的道统思想,并渗透到中国政道与治道。以学界的研究成就来看,对于夏、商、周及秦汉的政治体制,无不延续道统思想来建构文化,尤其是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和谐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大同”理想的传统,并成为政治、社会、文化建制模式的基础,由此延伸至以人为本、以礼为序、以德为治、以乐为和等社会理想。因此,在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历史延续上,不只要从各位思想家、政治家的文化传统中来梳理典章规范和天道观念,还要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模式,从融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中国精神的来龙去脉。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出色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其意义在于对当下中国人怎么样理解和应付日常的问题,迫切需要从“精神基因”的整理中来提炼“活的传统”,以至于治道。从“阴阳”悟于“道”的逻辑思维中,遵循天道宇宙论、道德修养论和道义实践论的思想体系,并从知行合1、经世致用中来坚守“礼仪、孝悌、仁义、自强”精神,并从出色的文化基因中来撷取当代中国精神中的“活的传统”。当下,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影响下,对“天理”、对“良心”的追求依旧是中国普通大众心灵中最淳朴的传统思想,并成为日常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精神与文化认可。这类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活的传统”,在体现中华民族特有些民族性、乡土性上,更是承载着对民族生命及文化延续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财富。透视中国精神中的文化理想,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层面等范围来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诉求,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中国家庭、社会团体成为中华民族“活的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德性精神作为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社群、乃至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在出色传统文化世代相延中,渐渐形成常见老百姓对文化的信仰和敬畏。如儒家的“耕读传家”、“崇尚学习”,将通过学习来获得君子的人格,收获“塑身、云筑网、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向往,者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在吸纳、融合、继承中达成现代意义的自发传递。
3、结语
中国精神不是纯粹的时间历史逻辑,更多的是体目前当下的意义性逻辑。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质来深思中国精神的现代意义,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衔接上来摆正两者的关系。中华出色的传统文化势必以实践诉求为历史导向,并反映在不同时期下的“大同”、“小康”、“治世”理想,具备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为深思中国精神提供了有序的实践路径。当代中不是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国的当下与将来更有别于西方。对于中国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在缺少文化自觉和自我理想首要条件下是很难达成的。法国学者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由来》中提出“古希腊的思想形成于几何学性质,也是构成西方理性思想的由来”。从中可见,几何学式的世界观讲究对称和均质化,也就是对“等距”关系的抽象与概括,体现出西方精神常见性的平等观。而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及世界观,既非空间上的弯曲,也非时间上的平直,以家庭为最高伦理实体的中国社会,将家庭作为维系情感的核心纽带,并以人与人之间家庭式的情感和谐来构成国家。所以,从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借鉴中,大家不可以照搬西方的文化模式,而是应该从德性精神的历史延续性和传承上,依托中华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与时俱进,从中西方文化交融中来挖掘中国精神的年代性内涵,来破解当下中国面临的精神文化传承中的新困惑和新矛盾。关注人的精神及心灵问题,坚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然性、伦理性统一中强调人的整体性,增强民族自觉和自信,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来确立完满的精神人格,使之成为衔接当下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