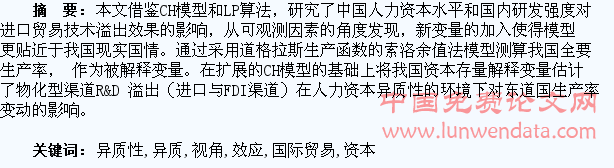
1、引言
当今全球在历程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一系列金融动荡后,技术与研发升级问题成为城中热话,但自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一国的R&D开发不再是本国问题,海外一流的技术也通过间接渠道在潜移默化发挥着用途,要想成为世界强国,不只要在自己有利资源的基础上提升生产率,还要继续吸收他国值得借鉴的经验,努力全方位、深入、系统的自我健全、升级。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研究国内怎么样通过FDI与进口途径渗透技术外溢,并且加入人力资本异质性衡量外溢成效。
2、文献综述
基于Coe和Helpman(1995)的国际R&D溢出回归剖析框架,此后的很多文献都是打造在这个基本剖析的框架之上而不断扩展和丰富的。Lumenga-Neso,Olarreaga和Schiff(2001)在计算外国资本存量事考虑了“间接”贸易的R&D溢出效应,即两个国家之间即便没有相互贸易的状况,只须他们分别与第三国进行贸易,这两个国家也会从他们获得技术溢出。Schiff,Wang,和Olarreaga (2002)运用进步中国家产业层次的数据也证实了“间接与贸易有关的R&D溢出”的显著性。另外Schiff和Wang(2004)曾在CH模型基础上加入教育和政府管制水平的有关变量,并得到了极具启发意义的结论:教育和政府管制水平的提升可以直接致使TFP水平的提升;在R&D密集型产业,教育和政府管制还通过与海外技术溢出的相互用途提高TFP;因而对贸易、教育和政府管制政策的通盘考虑会对TFP的增长带来更大的影响。国内方面,赖明勇、张新等(2005)借助1996―2002年间国内30个省市的经济数据,考察了分别以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衡量的技术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比较了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种途径的技术溢出成效。赵伟、汪全立(2006)通过在基本模型中添加度量吸收能力的交叉项,考虑吸收能力之后交叉项系数为正。对国内技术进步有积极推动作用,而单独的海外技术溢出变量系数为负,不利于国内技术进步。申嫦娥(2009)和韩峰、隋杨(2011)分别就亚太发达经济和台湾对内地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做出了实证剖析。
就现有文献来看,有学者着重健全海外R&D存量的算法,有将样本扩展到行业和企业数据,有加入多个控制变量来健全对回归方程的精度,鲜有侧重单独研究人力资本异质性对该模型的影响,所以笔者借此研究人力资本对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全要点生产率的影响。
3、基本模型介绍与评价指标
因为本文主要剖析的是人力资本对国际贸易溢出的成效,所以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方便性,选取OECD诸国的全部GDP作为整体取值,以国内每年从OECD国的所有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作为分子,而OECD国的研发存量基本同国内研发存量的计算办法,研发支出可以参考OECD官方数据统计得出。
(二)借助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全要点生产率。
1资本存量:可用现在广泛用的测算办法――戈登史密斯(1951)
2基年资本存量:因为有关数据不完整与测量办法的差异,国内并没一个可以依靠的资产普查与基本存量,所以这里又需要用到折旧―贴现法(Hall and Jones 1999)。本文鉴于其他基础数据的可获得性,以1991年为基年。
(三)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同样采取永续盘存法。
(四)海外资本存量
(五)人力资本
一般文献都是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国内的教育一向进步不平衡,区域间的人力资本差异更是巨大,不光是存量的差距,还是水平的差距。所以在通过FDI或者贸易途径吸收海外技术也要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问题,毕竟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对于技术、常识的获得能力不同,此处通过引入教育加权变异系数测量国内人力资本异质性特点,代入到CH模型中,测试会不会对全生产要点产生直接影响。
1人力资本水平(HC)
2人力资本异质系数(RDHC)









































